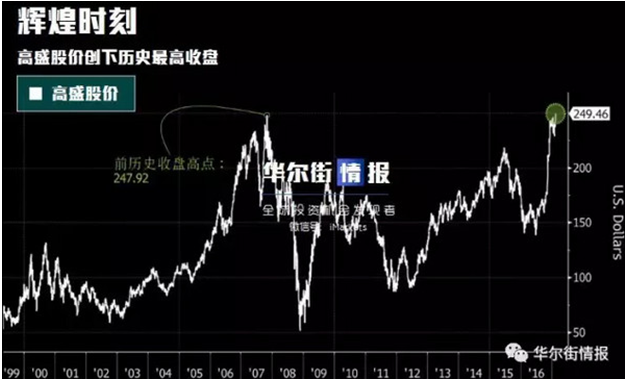本期《有色眼镜》嘉宾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自1996年起任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至今,以每周发表的专栏和多部著作享誉学界与政界,被公认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宏观经济评论人之一,跻身《外交政策》杂志评选的全球最重要的100位思想家之列。他在世界顶级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中人脉广泛,是达沃斯等国际论坛上的常客,支持全球化和自由市场。他多年来密切关注中国经济,过去25年间几乎每年都到访中国。本次访谈,我不仅请他以经济学家的视角对中国经济做出研判,也试图与作为媒体人和思想家的他一起探讨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中国模式、以及西方在2016年之后的路径选择。以下为我们的访谈实录:
王昉:马丁,作为FT首席经济评论员,长期以来你都是一个中国观察者。对你来说,是否存在一个“中国谜题”,使得中国很难描述或者评论?
沃尔夫:中国是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国家,一个人对于这样一个国家的认识,必然是非常片面和不完整的。中国的语言文化和西方都不同。我始终提醒自己,我可能永远无法彻底懂它。人们总是问我是否了解英国,我的答案是,我不能,更别说中国了。
一个人恐怕永远无法彻底了解一个地方,但中国也确实存在一些让人着迷的、专属于它自己的“谜题”。比如你们经历了一个非常快的现代化过程——一个非常古老的文明,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推进现代化,这个现象独一无二。此前也有其他国家实现过快速现代化,比如韩国,但中国经济规模远大于韩国,这种规模增加了它的复杂性。
最后,对于西方来说,最大的“中国谜题”是,这种现代化进程是由一个共产主义政党领导的。你知道,对我们西方人来说,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意识形态,它来自西方,却被西方所拒绝。现在共产主义出现在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宣称它是共产主义的,我们很难理解这意味着什么。这真的可能发生吗?它又是怎么运行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中央集权的,原则上来讲显然是非民主的,但同时中国又有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这种奇怪的对比也是独一无二的。你怎么能在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谜题。
大多数西方人的假设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人变得更富有,出现更多中产阶级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中国在政治上可能会变得更像西方。这一过程确实在韩国和日本发生过,但好像还没有要在中国发生的迹象。这是一个真正的谜团。
王昉:西方经济学家发展出一整套经济学原理、价值和标准。当你报道和评论中国时,会使用同一套原理吗?还是说会用一套完全不同的方法?
沃尔夫:我不是奉行经济帝国主义的经济学家,我不认为经济是一切,但我认为有些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我认为经济学的核心原理是逐利,也就是人们寻求利益的动力。这不仅存在于公司中,也存在于个体。这个理论用于中国时,解释力很强。中国人有很强的逐利动力,如果你观察全世界的中国人就知道,他们运营企业的能力非凡,在商业上极富天赋。
我认为用关于发展的标准经济学原理来描述中国没有问题。这一原理的核心就是,经济增长由人力、资本和创新推动。在资本这一块,中国在我们所有观察的国家中,拥有最高的投资率;在人力这一块,中国人对于教育也就是人力资本极其狂热;此外,中国也致力于创新和技术升级。所以这些经济学原理都适用。
中国经济当然有很多特色,其中一点是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在每一个大企业中都有一个党组织,这一点很特殊。我们需要搞清楚他们的角色,他们是怎么工作的,会怎么影响企业运营。但要知道,西方也有很多不同形态的资本主义,德国资本主义不同于美国资本主义,日本的资本主义又不一样。中国的不同之处,或许并没有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差异那么大。明白这一点很重要。
另外,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仍然相对贫穷。发展中国家有一些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特质,比如潜在的增长率更高。中国正在经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我们在西方就没有这样一个进程,因为我们已经高度城市化了。中国仍然有一个非常大规模的农业经济,这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不存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其他东亚国家很相似,但中国这一进程的规模和速度是独一无二的。
王昉:中国如此独特,而且在经济统计数据方面名声不佳,所以许多经济学家会用一套自己的方法,比如从猪肉价格分析中国真实的经济增长。你有这样的秘密武器吗?
沃尔夫:我没有。虽然我对中国某一特定年份的经济数据没什么信心,但我认为中国数据整体上是准确的。总的来说,我认为中国经济真实的波动性要比数据显示的更强烈,也就是说,在经济繁荣时,数据会低估增速,在萧条时,数据又会低估衰退程度。这背后有很多原因。首先,中国经济必须实现政府目标,所以数据上它总能“实现”目标。另外中国的统计数据发布得太快,没有人会相信,那么短的时间里能统计出准确的数据。即使拥有庞大统计机构的西方小国,也需要比中国更长的时间来统计数据,尤其是GDP,而且这些数据还会被反复修订,因此中国某一时期的统计数据不会太可靠,会低估短期波动。
但我认为,中国数据整体看还是可靠的。首先,你只需在中国四处看看就能感受到。我已经来往中国25年了,很明显它变化非常大。另外,我们可以用国际数据,比如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数据,来验证中国数据。中国的贸易增长是如此之快,尤其是在2007-08金融危机之前,很明显暗示着大规模的GDP增长。尽管逐月、逐季或是逐年的数据或许不是那么可靠,但整体数据还是非常值得信赖的。
至于我自己最喜欢的统计数据——我也观察了一些其他人的分析方法,比如有人专门研究所谓的“克强指数”——但我看待中国经济的角度有点不同。长久来看,一国的福利增长和消费增长是相互关联的,这是亚当•史密斯教给我们的。生产的目的是消费。我认为尤其是在过去的15年中,有一个越发明显的趋势,那就是中国有大量的投资被浪费了。有相当多的投资被算进了GDP,但它们可能没有为增加中国人的福利做出任何贡献。我认为更应该关注消费的增长。在中国经济繁荣时期,消费比GDP增速慢了一些,大概一两个百分点,这显示出在2010-2012之前的几年间,很大一部分投资驱动的增长是浪费性的。而现在消费增长反超GDP,我认为这是正确的趋势。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许多重要问题是GDP数据反映不出的,包括经济对环境的影响。在过去,中国GDP数据明显低估了严重污染和资源滥用。现在这方面好了一些。这一点,加上我刚才说的投资被浪费,使得GDP并不能很好地反映中国人的福利增长。
王昉:许多中国人感觉西方媒体对中国带有偏见,他们带着一种优越感来到中国,报道中国负面新闻的时候远远多于报道正面新闻。你同意吗?
沃尔夫:现在好像每个人都厌恶西方媒体。中国人对西方媒体的看法,和西方政治家对西方媒体的看法很像,甚至可能还不如后者那么敌视。
首先新闻业有一个特质,我想它也适用于中国,那就是新闻的消费者,也就是阅读和使用新闻的人,对于负面新闻总是比对正面新闻更感兴趣。如果世界上哪里发生了一起灾难,它会出现在媒体的头版;如果事情超级顺利,根本不会出现在媒体上。政治新闻、社会新闻也是这样。全世界新闻媒体都更倾向于关注坏消息,这正是人们讨厌报纸的原因之一。西方媒体这样报道中国并不特殊,它们报道自己的国家时也这样,绝大部分新闻都是负面的。
其次——这也许有点夸大——但新闻媒体认为自己是权力的监督者,要让权力对民众负责。如果掌权者说了“X”,媒体就要指出为什么“X”是错的。这在中国也许是有争议的,因为中国政府喜欢控制媒体,那些质问“你说中国是这样的,但你说得不对”的媒体就会变得很不受欢迎。但这也是一种普遍现象,并不只发生在中国,哪里的政治家都讨厌媒体。中国政府当然会对外宣称它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这些成就的确非常巨大,但中国还是存在很多问题。自然地,媒体就想四处查找问题,因为媒体就是喜欢“坏新闻”,尤其是当政府在歌功颂德的时候。
不过西方媒体怎么报道中国,我认为已经远远超越了媒体本身,而是关乎西方整体上如何看待中国。这就非常复杂,很难概括,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大部分国际主流媒体的记者是西方人,秉持美国式的自由主义立场,他们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一点本能地不喜欢中国的政治体制。我刚才说过了,我们认为共产主义这种意识形态难以理解和接纳。要知道,当年的冷战,正是一场民主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间的冲突,是意识形态的冲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政治体制是西方的对手,人们当然对它有所怀疑。西方民众还是认为民主更好,也许你不这么认为,但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最后一点,我时常问自己,西方对于中国的报道和看法,多大程度上是由恐惧支配的?这是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几乎可以肯定,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从而成为世界上居主导地位的政治因素,而中国又不是一个西方式的国家,将来也不会是,这让西方人感到害怕。西方人已经完全习惯了用他们的方式来统治这个世界,奇怪的是他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不想失去这样的地位,但很明显中国将改变这一切。大多数有智识的西方观察者认为,中国的崛起既令人兴奋也令人害怕,因为我们不知道这对我们的世界将意味着什么。
王昉:我们之前谈到了优越感。如果西方人确实存在这种优越感,那么在2016年西方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之后,这种优越感是否正在消失?
沃尔夫:很久以前,的确有人认为西方从根本上要优越得多,不论在文化上,甚至在种族上,中国无论如何也比不上。一百年前,人们的确有这种可笑的想法。如果你说的是这种优越感,那么三四十年前中国一些邻国的成功,就已经对它提出了挑战。比如很多西方人认为现代工业化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但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韩国、新加坡和香港的崛起,这种观点已经基本消失了,中国只不过从更大规模上确认了这一点。那些最成功的西方国家可能至今仍觉得自己更加先进,比如美国人肯定觉得他们的经济文明仍是世界上最优越、最有活力的,但他们肯定不像三四十年前那样如此顽固地确信这一点了。西方那种旧时的优越感已经荡然无存了。
和你的问题更加相关的是,我们曾经认为我们西方的政治体制、政治价值是世界的标杆,自由民主是统治世界的最佳方式,但我想发生在过去一两年间的事情,让我们对此也提出了疑问。我们肯定犯了一些大错,才会把美国总统的位置交给了一个完全不胜任的人。这当然会引发疑问:我们的体制还在运转吗?而且中国人比我们更有资格问出这个问题。
西方的确应该自问,我们是否还有自信的资本,但是我不认为,我们真的已经找到了怀疑我们西方体制的理由。我个人认为,西方转向中国模式完全行不通,我们也不会愿意这样做。问题在于,我们能否让民主机制重新充分运转起来,现在是问这个问题的绝佳时机。
王昉:我看了你去年写的一些专栏文章,你显然对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非常忧虑。中国人对西方发生的这些事情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方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失败了,另一方则认为,这些事情正说明民主体制在运转。你怎么看?
沃尔夫:两种观点可以说都是正确的,因为这些事件背后的原因都一样,就是政府没能满足民众的需求。
我个人的观点是,那些新近掌权的民粹主义者们,尤其是在美国的那些,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好的答案。如果你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你可以说,如果这些人解决不了问题,他们会失败,然后选民们会选出更能解决问题的人。这种乐观看法,表明民主仍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体制,它不完美,但能适应现实,最终能产生更好的结果。而且相比于暴力革命,民主肯定是实现目标的更好方式。捍卫民主最有力的论证是,当改变必不可少时,民主可以实现权力的和平交接。在一个非民主国家中,如果没有选举,如何保持政权的合法性?当政策需要作出改变的时候,如何改变?如何防止官僚体制僵化?这些问题,中国都需要思考面对。而我们西方的问题是,我们能否选出有能力的领导人?如果人民选出了傻瓜怎么办?在民主政治体制下,这种风险很大,也确实发生了。
对于那种说资本主义和民主已经失败的观点,我会说,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失败在某种意义上是联系在一起的,都肇始于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本不应发生,是政府的金融市场政策失误所致,凸显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而不稳定性是资本主义运转中的一个重要特质,要靠民主来解决这个问题非常困难,至今依然很难,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存在张力。我们完全可以问,我们可否只要资本主义,不要民主?我觉得或许短时间里可以,但长远看来非常难。如果我们既要资本主义又要民主,我们就要想办法让资本主义体系变得更加稳定,让民主制度能够选出更有能力的领导人。我觉得这是个挑战。
长远来说,我不相信专制的、或者非民主的资本主义,可以持续取得成功。世界上几乎没有个人收入跻身发达水平的国家是专制资本国家的例子,中国也不是,因为即使到今天,中国仍然是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如果五六十年之后——我是看不到这一天了——如果那时中国成长为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还能维持和今天大体一致的政治体制,我会感到非常震惊。我倾向于认为,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最终还是需要一些民主化过程的。问题只是在于,我们能否让这个体系有效运转。
王昉:谢谢!现在是快问快答环节。请用一句话来回答下面的问题。你还没有采访到但是最想采访的中国人是谁?
沃尔夫:我想应该是中国国家主席吧
王昉:如果你被召唤到习近平的办公室,给他一条治国建议,那会是什么?
沃尔夫:我的天。我也许会说,在经济和政治改革上放手一搏吧。
王昉:经济学家总是做各种预测,你当然也会做。你对中国的预测是否失误过?
沃尔夫:失误过。我对中国最大的误判是,我低估了中国领导层在中短期管控经济风险的能力。
王昉:作为专栏作家 ,你从每周的写作、发表、与读者交流中,得到的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沃尔夫:很简单。能自由地向很多人表达自己的观点,这让人非常快乐。